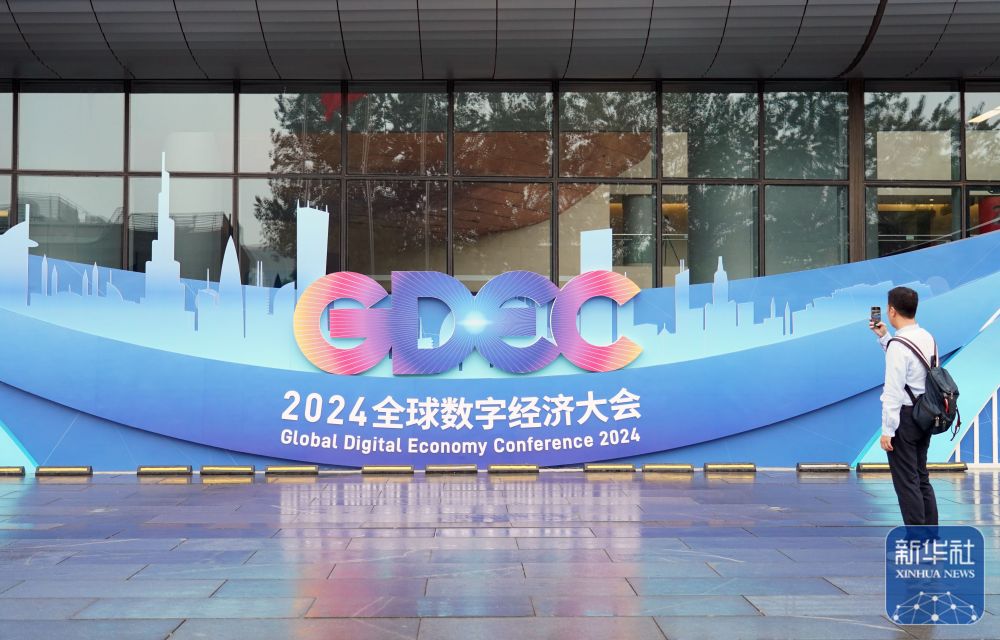5月28日,由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办的安大史学新讲堂特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主讲,主题为《现代文化建设视野下的中国大运河文化》。讲座由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盛险峰教授主持,本文系讲座实录。
一、中国大运河从运输河道转化为文化体系的过程与原理
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这个题目不是有关“中国大运河”的历史研究话题,因为有关大运河的历史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论文和著作数以千计,大家都可以去检索阅读。今天我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中国大运河”作为“人类遗产”的话题,或者是一个与“文化遗产学”有关的话题。
(一)从“文化遗产”到“大运河”
文化遗产学是一个新学科、新领域。文化遗产学看上去跟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民俗学、人类学,包括工艺学、技术学、规划学等等有很大关系,涉及很多学科,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比较有趣的学术创新问题。当然,今天我们不是来探讨文化遗产学问题的,但我们使用的视角和方法是文化遗产学的,这其中包括遗产考古、遗产产生的历史追溯、物质遗产形态、非物质遗产形态、遗产保护利用及遗产价值评估等等。
如果我们把“文化遗产”当作一个“话语”的话,它就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资源,积累至今的年代有300多万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创造的文化距今320万年左右,那就有320万年左右的创造积累。当然,文化遗产主要的创造和积累的时间,大概从距今5万年左右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今天的所有行为,明天就会变成遗产,这些就会构成我们的一个认知对象。
文化遗产是人类的一种发展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跟自然资源的一个最大差异是:自然资源用完了就会枯竭,所以出现了很多所谓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但是文化遗产是永远不会用完的,反而是越使用,其价值就越大,其推动发展的动力就越大。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现代科学,调查、研究、保护、利用、发展文化遗产更是人类的一种现代化事业。文化遗产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根基,而现代社会实际上就建立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根基,主要在三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有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文化。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这三种文化都是属于一种文化遗产形态。作为构建了我们社会根基的一种对象,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遗产还是一种创新发展的资源。王巍先生就认为,(这种)创新发展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物质创新,是在自然的资源里边进行研究开发;但是也有另一种很重要的创新,就是向历史的发掘。我们每一次发现了一种文化遗产,就会运用它重新构建我们的观念,构建我们的社会结构,构建我们的文化体系。所以,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是奠定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方法。
文化遗产学作为一个领域和方法,产生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学者总结过,人类农业文明走过5000多年,尽管也有过国家战争、阶级冲突、民族矛盾、自然灾难、专制迫害等种种问题,但是总体上还是可持续的。18世纪60年代工业文明诞生,这使人类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今天缤纷多彩的物质世界都是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但是它也产生了各种严重的问题甚至是危机。农业文明时期的很多问题,今天还存在。但是工业文明产生了新的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及生态危机、资源消耗过快和能源危机、拜物教和金钱崇拜、市场剧烈争夺、贫富分化日益加大、信仰缺失、恐怖主义、高科技战争风险等。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危机,“校正”人类发展方向,从方法论上或者从根本上说是要问“人类怎么办?”不同的学科可能有不同的方案。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考古、历史、文物及文化遗产、博物馆、历史文献等学科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可以去做什么?”我们这些来进行专业学习的人,就是要去为人类、为国家、为社会、为我们的人民去解决问题,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让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更加安全地向前发展。我们要以“文化的力量”为人类寻求发展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肉体和心灵的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自然资源开发和文化资源开发的平衡、增量和存量的平衡等发展策略。我们的目的是不要让现代化这艘巨轮倾覆或迷航。
1972年6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the Human Environment)这两个文件。在《宣言》中提出:“人类拥有一种在能够过尊严和幸福生活的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负有为当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神圣责任。”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来源,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行动。我们应该注意到在1972年的这两份文件里面,它所讲的人类的环境权包含了两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生态文明;还有一个是人文环境,而这个人文环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遗产。如果离开文化遗产,我们这些人文学科是无以立足的。
同样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文化遗产领域中的一个里程碑。今天我们很多的文化遗产的理念,其实都是从这个时候变成世界的共识的。在通过《公约》的同一天,教科文组织议决了《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t National Level, of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这个建议提出:“在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中,为人类保存与其相称的生活环境,使之在其中接触到大自然和先辈遗留的文明见证,这对人的平衡和发展十分重要。”就是说在《公约》及其执行中,追求的是人的平衡和发展。下面又提出,为了让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整个社会的建设规划要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当代成就”。但是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必须纳入到社会的规划中,一个是“昔日价值”,就是文化遗产;还有一个“自然之美”,就是自然遗产。一个区域规划也好,一个城市规划也好,一个乡村规划也好,只有包含这三方面,才是一个最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安全的、均衡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规划。
按照经济学原理,那些不可再造的东西才最具有价值,具有唯一性的价值,所以在建设中间,当我们把很多的这种“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毁灭掉时,建设起来的就处于一个不和谐的、不安全的、不可持续的状态。这种以人类遗产为主导力量而追求均衡发展的先进理念,它的核心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机联系,以及文化与经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目前正在追求的理念。
然而,面对国际上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事业的蓬勃兴起,人们会问:我们为什么创造和需要这项事业?这难道是为我们自己吗?不是的。我们作为一个人,要对子孙后代负责,要对整个社会负责,要对国家负责,当然讲大一点要对人类负责。特定情况下的工业化、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了很多危机,我们从事文化遗产事业正是在抵抗这种危机。在现代科技支撑下,物质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大,而人类的精神生产力跟不上现实的需求。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资源,或者说一种软实力,就可以在此时发挥无可代替的作用。
“文化遗产学”置身于人类历史进程中并承载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让我们今天谈“中国大运河”这样一个同样宏大的主题有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中国大运河原本是一条在历史上使用了2000多年的人工运输河道,在21世纪时受到了“文化遗产”的思维指导,演化成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或“人类遗产”体系(2014年),演化成国家“五位一体”现代化方略中“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和主场(2017年以来)。
(二)大运河的“文化转变”
中国大运河从一条运输河道转化为“文化体系”的这样一个演化过程,需要多个条件。一是人类遗产事业的产生与发展,这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世界遗产运动为重点;二是由此引发的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从“文物观”到“文化遗产观”的转变,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是国家层面的重要法律;三是适应全球化的需要,1982年我们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2004年加入了《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到目前成为世界遗产大国;四是我国中央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且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核心体系,这使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成为一种国家的追求,一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实践;五是“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2017年迄今,党中央决策构建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以上这些就是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现代文化建设视野下的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来源。这个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含的区域,我用不同的斑块对八个省进行了一个表示。
“大运河文化”主要是指在大运河水系及流域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文化廊道体系及当代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发展体系。从大运河文化形态上说,有大运河物质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大运河文献形态的文化、大运河文化景观、大运河文化生态等;从时段上说有古代大运河文化、近代大运河文化、当代大运河文化;从类型上说有大运河水工文化、大运河水运及漕运文化、大运河城市与城镇文化、大运河乡村文化等。随着科学研究特别是大运河考古工作的深入,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类型被发现。这个是大运河沿线考古项目示意图。

大运河沿线考古项目示意图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大运河沿线考古工作,我们可以把它建成博物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遗址公园,可以把它变成乡村振兴或者特色古镇的一个建设对象,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旅游区,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内容。就是说,你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法,把这种大运河文化的发现变成一个“现代”的作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参与者”,变成一个人民可以去分享的历史创造。爱国主义、文化自信、创新发展,这些都包含在对大运河文化的考古中间。我们做大运河的文化建设行为,做这些“作品”,同样也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要成果。所以我觉得,自然科学学者和我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有着同样的目的,即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类的福祉,都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对于路径、行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有一个总目标,这是不可以放弃的。
我们来看泗州城。泗州城在唐宋汴河或通济渠进入淮河的一个结合部,后来在清康熙年间因为洪灾被淹到水里去了。我们2005年对泗州城进行了考古勘探,在下面发现了城墙,还发现了一些遗物,包括唐三彩等。所以考古学就把当年被全部淹没掉的一座城市,在地下一米左右深的地方发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大运河文化的一种发现。沿着明清黄河故道,当然它也和大运河有关,许多城市在历史上形成一个又一个黄泛性遗址,后来我称之为“灾难性遗址”。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人类应该认识自己的灾难性遗址,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所以人类应该汲取历史上灾难的教训,来更好地寻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式。
考古人又在淮安市发现了运河板闸遗址。板闸遗址中能看到在地下保存下来的一些地钉和其他遗存,这蕴含了很多工程的技术在里边。一段运河是怎么开挖出来的,包含了哪些科学技术,需要我们通过遗产学的方式,一个一个找到并说明。这样一来,我们大运河的这种技术系统、设计系统、智慧系统、工程系统,以及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管理系统、文化系统、城市和城镇系统,以及它的整个文化系统,就可以被一点一点寻求出来。如果我们摈弃这些东西,只是把大运河看成一个普通的运输河道,而不把它看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创造、一种文明成就,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谈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会灰飞烟灭。
我们把刚才讲的这个部分适当地展开一下。中国大运河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上半叶持续完成的巨型人工运河工程,包括先秦到南北朝大运河、隋唐宋大运河、元明清京杭大运河。它经过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省市,涉及数以百计的大中小城市。河道总长约3100公里(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其中主线长度约2681公里。它历经运输河道、南水北调输水通道、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几个阶段。今天它具备着生活、生产、文化、运输、供水、水利、旅游、生态、景观等综合性功能。我们今天谈这个大运河,是从文化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谈的。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大运河不仅仅是我们文化人的,它还是我们整个人民的、整个国家的,因为还有众多人民生活在运河两岸,众多城市与城镇分布在运河两岸。
我们提到大运河身份的变革,是在说大运河从经济性到文化性的变革。当年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申报对象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它的价值评估是:“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这些词是不是太夸张了?其实不是的。他们(世界遗产专家)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创造,都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都具有全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将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每个时期的伟大的创造都视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的财富。世界上也有其他国家的运河进入世界遗产,比如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拉卢维耶尔和鲁尔克斯主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英国庞特基西斯特输水道及运河等。可以说,世界遗产专家对中国大运河的评价是在全球比较视野下给出的,不是为了说给中国人听的,而是说给全世界人听的。
总体上看,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稳定政权、维持国家统一为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展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工运河发展的悠久历史阶段,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学术界对整个大运河的一种现代化视角下的评价、解释和一种价值肯定。
我们再对中国大运河文化价值做出一个总体认识:第一,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交通运输工程;第二,大运河是支撑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三,大运河是多样文化共生、共通、共荣的空间廊道;第四,大运河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纽带;第五,大运河是影响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最后,大运河是当代中国最宏大的国际文化“名片”。
我们再深层地来探讨一下中国大运河的价值。实际上,中国大运河的价值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运动机理之中。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的诞生地之一和东亚地区唯一的原生文明诞生地,作为世界原生文明延续到当代的文明奇迹,在这方土地上的所有自然大河几乎都是从西向东走向的,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等无不如此。这是古中国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地理背景的最大不同。东西走向的自然大河及其流域创造了古中国文明,给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诞生、发展与碰撞提供了运动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早期文明如尼罗河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文明、印度河和恒河文明都在北纬三十度这条线上,它们的河流都是南北向的,只有我们黄河和长江是东西走向的。这种巨大河流文化板块的阻隔实际上为农业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南下提供了极大的优势,使得农业民族获得更为安全稳定的文明发展空间。但东西向的河流也有缺点,就是容易造成南北阻隔甚至同胞分离: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时代等,几乎都会以淮河——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分裂。而且,因为自然气候、土壤、水量、农业品种以及民族、移民及人口分布等各种原因,中国存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而政治中心必须在北方的问题。
因此,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它就是“中国大运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土地上唯一的南北贯通、而且连通所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包括海洋的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网系统。这是大运河超越“上苍之手”重构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的伟大创造性所在,它也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不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因为至少从隋唐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再也不能离开大运河。
换句话说,大运河是切合中华民族需求、顺应中华文明内在发展规律、重构中国宏观山川水系、整合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伟大工程与动力体系。它的伟大性已经深深嵌入到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进程之中,并且还会深刻参与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进程之中。大运河的举世无比的文化贡献需要我们今天用历史细节慢慢揭示和体会,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触摸和感知。这也是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志与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价值所在。
二、中国大运河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运河的产生与发展,这个是历史方面的问题。这里还涉及到交通,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交通遗产。交通是人类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没有交通的不断开发,就没有人类的文明进步。而古代最便捷、最廉价的交通是水运。
(一)产生阶段
最早开凿的运河当属楚国庄王时期(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0年)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引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使长江中游的干、支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后来伍子胥率吴国军队伐楚,曾疏浚此河,故又称“子胥渎”。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两支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
春秋后期,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为攻越、征楚、伐齐,争霸中原,曾先后开凿堰渎(从太湖西接长江)、胥浦(从杭州湾北通太湖一带)、古江南河(南起吴都、北至渔浦)、百尺渎(由吴都通往钱塘江北岸)、邗沟和菏水等数条运河。越国也开凿了浙东运河最早的一段,由绍兴至上虞,又名“山阴故道”。
吴国及其开凿的邗沟,通常被认为是大运河的“逻辑起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长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
公元前482年,吴人又从菏泽引济水入泗水,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这样,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水系就连为一体了。战国时,魏国开凿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连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濮、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其中通泗的运道成为后来汴水的一条重要支流,它最早把徐州纳入了后来的大运河体系。
邗沟、菏水、鸿沟等局域运河的开凿,使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早沟通“四渎”的区域性运河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一些运河都被称之为“沟”“渠”“水”“河”等等,一直到北宋年间才出现“大运河”这个概念。在这里我想重新厘清一下:使用“中国大运河”或“大运河”来称我国横贯南北的运河是准确的。宋代使用“大运河”这一概念时,它指的是隋唐至北宋的运河及河道流域。元、明、清使用“大运河”主要指元代及此后形成的运河及河道流域。显然,“大运河”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被史籍和我国现代历史著作所界定。用“大运河”简称或统称“中国大运河”是有依据的。而“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三个概念,包含的历史地理河道走向和文化涉及范围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经常读到一些张冠李戴的文章,是因为概念搞错了。概念是人类发现和创造出来的揭示事物内涵和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概念用得不准确,就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所以我们要准确地界定概念,并且准确地利用概念,然后才能深入到概念背后的体系中去。
(二)发展阶段
纵观2000余年的中国大运河修建史,大运河起源于先秦,初步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繁荣于两宋,兴盛和终结于元明清时期。我把大运河的发展阶段具体划分为六个时期:一是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全国局域运河初步发展时期,二是隋唐全国性大运河全面形成及发展时期,三是北宋全国性运河繁荣及南宋局部发展时期,四是元明清京杭大运河高度发展时期,五是近代大运河衰弱时期,六是当代大运河文化建设复兴时期。大家有没有发现大运河跟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命运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那是因为这个背后隐藏的就是从天道到人道再到文化之道的一个内在的共振关系。
秦汉时期统一王朝的建立,为运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秦王朝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联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开凿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疏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令三千囚徒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系统。
西汉时期,先后修建了由长安直通黄河的关中漕渠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荥阳漕渠,重点整治了黄河三门峡的砥柱之险。荥阳漕渠为鸿沟水系的改造利用,它由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出,分为两道:一道由鸿沟旧道通颍水,至寿春入淮;一道由陈留东南行入泗水,再南下通淮,是为汴渠。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西汉强大王朝的存在,离不开运河的支撑。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为巩固统一国家,必须大规模地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这一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河网。
唐朝大运河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局部变更和整修而形成。主要运河工程包括对汴渠、山阳渎、江南河和永济渠等进行多次疏浚、整治,开挖三门运河、涟水漕渠、湖州运河、仪征运河等。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大唐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奠定了深厚基础。
这一时期,今安徽省淮河以北进入大运河主运道。这一段主要是通济渠,当然通济渠的形成还有待研究,有一些问题目前尚不很清楚。我们今天研究文化的问题,一定要重视这样的基础研究。离开基础性研究、细节性研究、真实性研究、过程性研究、变化性研究,这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这些做基础研究的人搞错了,那博物馆谈的也就谈错了,谈大运河的中国故事也谈错了,政府部门的决策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去做这个基础研究。
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首都的生命线。北宋依然沿用隋代的运河系统。在重点经营汴河的同时,相继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广济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以及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黄河、汴渠、蔡河、五丈河合称“漕运四渠”,共同构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络。北宋运河系统的发展标志着漕运中心由洛阳转移到开封。由于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构成的南北运河的地位日趋重要,实际上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每年由此输往京师的漕粮达600万石。
这一时期的大运河主运道也在今安徽境内。隋朝的通济渠、唐朝的汴渠、北宋的汴河都经过今天的安徽,为这三个王朝北方与南方的统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沟通、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连接发挥过重要作用。大运河安徽段现在基本呈遗址状态,而不是活态运河,但是它在隋、唐、北宋三代曾经创造过文明辉煌。这也是今天安徽成为“大运河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为大运河安徽段的发掘、保护与文化公园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全国性运河网络发展受阻,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这时的江南运河成为南宋王朝的生命线,浙东运河得以进一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网络逐渐形成。有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才在强敌压境的态势下得以偏安一隅。

京杭大运河(示意模型)
公元1194年发生“黄河夺淮”事件,发生在淮河流域的豫东、皖北、苏北和苏中、鲁西南地区黄河洪水泛滥之地,时间长达661年。在此期间大运河深受其害,经济社会影响极其深远。
再到元朝,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元大都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为确保这一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最后的高峰。
近代以降,大运河进入衰弱时期。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结束了长达661年“夺淮入海”的局面,京杭运河被拦腰截断,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海运、河运全部废止。自此,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终结。
民国初年,曾对江北运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后因军阀割据、财政匮乏、技术缺失等因素而陷入停滞。抗战时期,运河区域位于沦陷区,更无法进行管理与治理,甚至很多河段已淤塞不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仅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而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一直到20世纪结束,人们对大运河的价值认知,还是停留在运输、水利等原始功能上。
这种状况一直到21世纪的头十年才获得改变。随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建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相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生、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今天讲的大运河文化,实际上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创造,这些创造都累积在大运河流经的这八个省市的空间里边。实际上大运河不仅仅是八个省市的文化,大运河的文化是全世界的。曾经走过大运河的这些人,像马可波罗,像马戛尔尼等等,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他们在大运河上走过,把中国大运河写进他们的书里边,使得大运河文化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大运河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它涉及的历史与文化是世界性的。
三、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认知
第三个问题是对大运河的价值展开来谈,即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认知。我们说以下几点。
第一,大运河是中国的政治河、经济河、文化河。
首先从政治角度去看,它是一条“政治河”。大运河的第一功能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国家文明,包括军事力量调度功能、供应首都中央物资所需的漕运功能等,是为了国家统一、国家稳定、国家治理,为了不同区域的相互整合、沟通和互动,为了不同民族的交往与凝聚,为了国土安全等等。为此,历代大运河的开凿、修理、管理等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予以主持,如夫差、杨坚、杨广、忽必烈、朱棣、康熙、乾隆等。在唐朝中期之后,大运河就成为支撑首都和中央运转的生命线。
当然,大运河也是“经济河”。包括国家经济和民间经济,如大运河及其联通的自然河道沿线和沿海区域资源的开发与流通,盐、渔、粮、丝、棉、茶、瓷器、木材、药材、砖瓦,各地土特产、餐饮业、娱乐业、服务业等都在运河沿线进行生产交流贸易,多种新的经济业态得以成长,大批的城市、城镇得以成长,农业渔业得到开发,税收得到保障。大运河是推动我国国土“胡焕庸线”现象形成的重要力量,这条线已经很少被提起,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说大运河是“文化河”,是指大运河沿线的各种文化遗产和文化成就的诞生,如城市文化、集镇文化、建筑文化、手工艺、教育、雕版印刷、书画、科学技术、文学、园林、饮食、戏曲、音乐、故事、民俗、宗教、文化人才等大量涌现。大运河沿线交通的便利、信息的交流、经济的繁荣、人才的来往、物资的流动、文化的碰撞都带动大运河沿线文化趋向发达,使之形成中国文化的富积区。
第二,大运河使得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海上丝路与草原丝路、天然运道和人工运道、经济基础和文化创造相互沟通、融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奇迹。
至少从隋唐开始,中国的首都如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南京等都不可能离开大运河,南北政治中心必须与大运河相连接,才能获得首都的生存保障和国家政治中枢正常运转的条件。海上丝路中的遣唐使、元代马可波罗、明代利玛窦、苏禄国王、清代马嘎尔尼等海外使者无不与大运河发生关联。中国外销的瓷器、茶叶等商品也多由大运河集散外运,中外沉船考古,如印尼黑石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等,可以充分证实这一历史过程。
大运河把唐代青龙镇、黄泗浦、掘港、扬州、涟水、楚州、海州、登州、宁波,宋代杭州、温州,元明清的上海、南京、天津等通海港口城市或集镇组织在一起,形成海上丝路的大通道,与陆上丝路相互连接,使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汇聚通过大运河得以顺利实现。当然这种沟通也有长江、淮河、海洋的广泛参与。
第三,大运河得以成功,是由于中国先民充分利用了天然运道,把人工运河与天然运道相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智慧和特征。
中国河流多为东西流向,如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等,人工开挖的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正好可以把它们打通连接起来,形成东西、南北运道相互交叉的最便捷的运输体系,首都——运河——天然运道——地方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每一个集镇和乡村,这是一种贴近实际、高效低价的工程思想及创造。在不同运道的连接之间,涉及许多水利水运工程技术问题,在每个连接点上,不同流域的分水岭处,都有诸多的智慧性工程杰作,如淮安、扬州、镇江、仪征、汶上等地保存的相关工程遗产特别丰富。为此,大运河作为人工河流,之所以有强大作用,是因为它借助于数以千计、万计的自然河流、湖泊、海上运道的优势,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系统,支撑着一个大国的物流体系。
同时,沿着水运道路,还有陆上驿道的修建,使之形成水、陆相辅相成的行水供水系统与交通系统,使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大国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水陆皆备的交通命脉,使大运河沿线区域在隋唐时代至明清时代长达1000多年时间里成为中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当然,此前的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两汉、三国至南北朝等时代积淀形成的各区域文化及局域性运河恰恰为大运河时代的到来、为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人才的流动创造了坚厚的基础。

2022年3月30日,江苏扬州,京杭大运河货船往来。
第四,大运河是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结构的重大力量。
中国5000年文明进程中,早期的中心还是在中原至关中的区域。到了唐代,出现“扬一益二”,长江流域经济占主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明清江南区域成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形成“胡焕庸线”所概括的现象,在这条线以东区域,大运河正居其中。这种现象一直深入到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黄河生态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等国家经济文化战略格局,支持着当代中国“T”型、“一带一路”交汇等发展空间结构的形成。
大运河一线的城市带,即从北京到杭州、宁波,仍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创造这种现象的历史力量即来自千年流通的大运河。今天的“南水北调”东线、贯通中国南北的“运河文化生态大走廊”仍然在大运河一线。这也正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所能找到的历史创造与现代文明高度关联、古今一体,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让历史创造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契合点。
第五,大运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内在关联性。
古代大运河代表着农业文明的辉煌,是水运时代、农业文明时代的生命线和能量来源;工业文明时代,大运河走向衰弱,1905年停止河运,而现代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代替了河运,直到20世纪末。现如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提出,使得大运河现状文化生命体的深厚博大,其文化资源蕴含的巨大文化能量可以应时代之需得以释放,大运河沿线巨大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交通运输价值、线状文化空间的联动分享价值、新型服务业的协同创造价值等都将得到充分发挥。大运河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复兴形成内洽、共生、互动的关系。
第六,大运河文化带是我国当代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长期以来,大运河沿线成为我国东中部经济文化发展的“脊梁骨”,在我国经济文化生产力布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承载着丰富文化资源和产品的“大运河文化带”必然强化这一传导和辐射功能,显著改善地缘文化经济。
最后,我们再次提到,“大运河文化带”及“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是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复兴及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它对推动中国东部和中部区域的“大运河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运河本体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与各类文化遗产的利用,特别是对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本文由查紫贤(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彭若瑜(安徽大学文学院)整理,黄文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夏晨曦(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