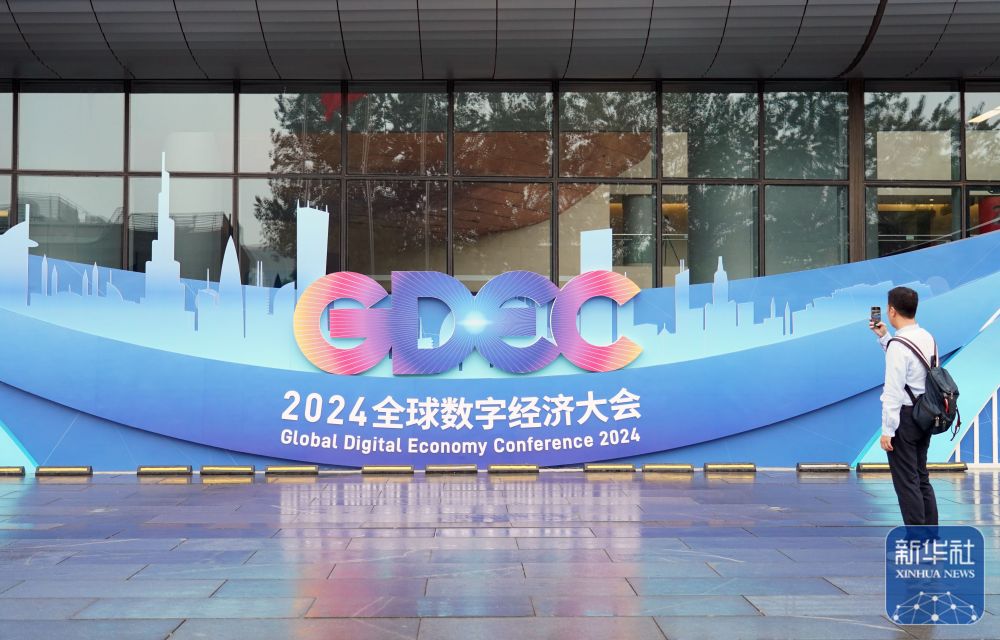喜马拉雅南麓的墨脱树蕨。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2017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2018年9月,首期研究成果在拉萨发布,主要涉及青藏高原的最新隆起研究、气候变暖变湿引起“亚洲水塔”加速液化和失衡、青藏高原变绿背景下的潜在风险、青藏高原天气气候效应和大气研究等。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将持续5年至10年,目前仍是进行时。而属于完成时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有些遥远了。
我们需要把时光回溯到40多年前。
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成立,拉开了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的序幕。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
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以揭示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科学目标;4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则是一次“科学大发现”,是中国第一次用系统的、科学的方式,丈量地球第三极。
中国科考的空白

青藏队队员在科考途中(左二为孙鸿烈)。
“到1907年1月为止,我们对行星面上的这部分与对月球背面同样一无所知。”这句话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在他的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之中。“行星面上的这部分”指的就是青藏高原。
这句话说得有些夸张,很大程度上是斯文·赫定在自夸,凸显他的成就。不过,他确实有资格这样说——斯文·赫定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把科学考察的概念带上青藏高原的人。
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
“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
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蜚声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玛旁雍错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
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他对此始终心有余悸。“那是人和牧群都无法生存的地方,在那里时刻都感到有如产妇难产之痛苦”,多年以后,斯文·赫定这样写道。
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只能在达尔果神山向拉萨的方向遥望一下而已。
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建,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式的传奇人物:植物学家刘慎谔和气象学家徐近之。
刘慎谔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年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后,独自一人取道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谔带回了两千多号高原植物标本。
徐近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3个月,徐近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无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镒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
地质学家孙健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健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
那时的孙健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
“任务带学科”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写道:“英俄日窥我蒙藏,探险之士,前后相望。夫以我国之土,彼却不惮险阻,卒能揭其真相以去。而我以主人翁之资格,反茫然无所知,宁非奇耻。”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近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
尽管如此,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科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
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科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一起向西藏进发。
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五十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科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鸿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些成果,其实可以说是西藏工作队的“附带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举办培训班、训练农业干部;了解考察区域的农、林、牧业问题,指导建立农作物和园艺试验场等等。这些实用的、有明确现实指向的任务,他们当然完成得很好,但是与他们本职的科学研究相去甚远。
在1973年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启动之前,中科院组织的青藏考察,大多与西藏工作队的这次考察类似,并非纯粹意义的科学考察,科学研究的内容服务于现实的某项任务,“科学搭了任务的车”。
这并非青藏高原考察所独有。大规模的、综合性的考察方式,在当时被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为了阐明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进行长期开发规划的优越的工作方式”。显然,这并非纯粹科学考察的定义。
1956年“向科学进军”,中国科学界就提出了“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同年,中科院成立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综合考察的组织和协调。这个机构在中科院的历史上地位特殊,它曾经一度由中科院和原国家计委双重领导,既负责组织协调,又从事学术研究,囊括了“任务”和“学科”双重责任。“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实际上表达的是中国科学界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初衷。
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藏高原考察来说,“学科”确实是被“任务”带着走的。最大也最多的“顺风车”就是登山运动。
登山科考模式,即登山运动加科学考察,是新中国首创。共和国的两位元帅常被搭车登山运动的“老青藏”们感念。
第一位,当然是登山科考的首倡者贺龙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
登山科考首开先河是1957年。此前一年,中苏联合攀登西昆仑主峰慕士塔格峰成功。中国在庆祝,西方媒体却在说风凉话:中国人“是被苏联人扶上去的”。
谁说中国人不能自己登山?贺龙元帅一手推动了中国登山队和中国登山协会的创建,决意组织一次中国人独立的登山活动,目标锁定贡嘎山。邀请科学工作者参与登山,正是贺龙元帅在这次登山活动前提出的。他说:登山仅仅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登上峰顶报道一下就结束了。但有了科学考察的内容呢,就不会有完结,意义又大又长远。
首登贡嘎山,登山队牺牲了4名队员,其中一位是地球物理与气象观测专业的北京大学年轻助教丁行友。这项事业一开始就展现了它残酷的一面。参与这次登山科考的崔之久,撰写了考察成果《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的第一篇研究论文。
自贡嘎山以后,登山科考成为固定模式。国家体委和中科院这两个机构在这个领域携手攀登。每次登山科考,几乎都是科考人员提供科技助力,登山健将在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代为采集标本、测量数据乃至做实验。
1968年,我国组织第二次攀登珠峰。科考险些被排除在这次登山之外。聂荣臻接见中科院相关领导,谈到珠峰考察时说:“补点(考察)我赞成,要搞就搞好,搞彻底。”于是,中科院科考人员再一次随队攀登珠峰,登山科考的模式也得以保持下来。

青藏队在进藏途中遭遇大滑坡。
“避风港”
1961年,孙鸿烈从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调入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分配给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进藏。此前一年,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成立,孙鸿烈担任了学术秘书。从此,孙鸿烈结缘青藏高原,迄今已躬耕半个多世纪,是我国青藏研究的灵魂人物。
如果条件允许,孙鸿烈在1961年就能够沿着父亲未竟的足迹,在青藏高原上走得更高、更远——他的父亲,就是发现了中国第一块油田、第一批翻越祁连山南北完成地质填图的孙健初。
如果条件允许,中国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可以把开始时间提前十余年。孙鸿烈参加的西藏综合科考队,从1960年就开始了对西藏的考察。
但是,现实没有给出这样的可能。
1960年起步的西藏科考“生不逢时”。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全国经济困难,西藏科考尚未完成野外考察就已经无力支撑。1962年又爆发了对印自卫反击战,西藏科考不得不中途夭折。学者们只是结合国家需要,在局部地区开展了部分工作。
而且,那次考察的目的在科考队中就有分歧,孙鸿烈觉得青藏高原研究还近乎空白,首先要调查积累基础资料,研究它的自然规律。而当时的主要思想是把考察定位在应用,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有哪些矿产可以开发之类。孙鸿烈带领的小组研究垂直地带分布规律,竟被批评“路线错误”。
幸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的竺可桢,化解了孙鸿烈心中的块垒。竺可桢特意听取了他的汇报,反复问询、关注的,正是孙鸿烈收集的基础数据。可惜天不假年,1973年,我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启动,一年后,竺可桢逝世,未能看到青藏科考的成果,完成夙愿。不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竺可桢野外工作奖”,第一届就授予了青藏队。
“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青藏科考没能完成,但中国科学家们探索青藏高原的愿望并未泯灭。他们在等待着登上青藏高原的机会。孙鸿烈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他一等就是十年。
“文革”爆发后,集中了中国科考专家的“国家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陷入瘫痪,后被并入中科院地理所,业务骨干大多去了五七干校。
孙鸿烈被分到了湖北五七干校,种庄稼、修房子、跑运输……期间被抽调到青海的一支考察队,调查宜农荒地资源和草场资源。考察结束,原本要重回干校,但孙鸿烈接到通知,返回北京,到地理所上班。
能够重回中科院,无疑令人兴奋。孙鸿烈兴冲冲地赶回北京。他获任地理所综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组副组长,接到的第一项工作是到兰州参加珠峰科考总结会。孙鸿烈的专业是土壤,又没参加过珠峰科考,和珠峰科考总结会本不沾边儿。但是,就像此前的登山运动带动着高原科考一样,这次珠峰科考总结会,给青藏高原科考带来了最重大的一次机遇。
原来,“文革”中万马齐喑多年的基础科学研究,在1972年获得了一次转机。此前不久,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当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向周总理汇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工作,周总理意见很明确:还等什么!科学研究要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往高里提。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醒要注意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提议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在科学考察领域,还有什么比几乎是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更基础呢?中科院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次机遇,把青藏高原科考提上了议程。1972年7月召开的珠峰科考总结会,在总结之后,就是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长远计划。
孙鸿烈参加此次会议的任务,是起草《中国科学院1973~1980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
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鸿烈立了大功。
青藏队,即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
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希吾担任队长。孙鸿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
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科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青藏队是避风港”,很多人这样说,但远不止如此,青藏队更是梦寐以求的实现科学理想的舞台。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那些曾在“运动”中颠上抛下、业务上赋闲多年的专家们奔走相告,争相报名。
名额有限,上过高原的获得优先权。同样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水文专家章铭陶,报名时才发现,自己最适合的岗位已经有了人——地质所的郑锡澜,那是参加过1960年珠峰科考的老将。章铭陶心有不甘,思来想去,找到个新的领域——地热。青藏队组队时,因为规模较小,尚未考虑地热问题。章铭陶向孙鸿烈请缨,参加青藏队,搞地热,填补空白。这个理由足够充分,章铭陶最终入列。他也真的在青藏高原的地热考察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用喜马拉雅地热带填补了世界地热图的空白。
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并非中科院在编人员,本是北京林业大学的讲师。“文革”中,北京林业大学被下放到云南丽江,图书馆藏书堆放在昆明的运输站,李文华作为留守人员驻站,伙食采买之余,就趴在书堆上翻书,还在昆明一带采集了大量标本,就近请教昆明植物所世界级植物学家吴征镒。那时吴征镒正处在批斗后被“晾”期,格外有闲也有心去指教他。
得知组建青藏队的消息,李文华直接找到相知多年的孙鸿烈报名。他本人专业资质优势明显,成了首批青藏队员中为数不多的中科院之外的专家,并担负森林组组长之责。
吴征镒的另一个学生武素功,是首批青藏队员中最后一个入围的。其实当时青藏队已经“满员”,但是藏东南考查对植物学专业的需求很大,临行前才仓促加了一个名额。吴征镒得到消息,让武素功搭上了“末班车”。那可真是“末班车”,他直接从昆明到青藏队的集合地成都报名,见到孙鸿烈后连一杯水都还没喝完,奔赴青藏高原的汽车就出发了。
吴征镒本人,早在抗战时期就自己考察过白马雪山。青藏队组建时,按说该有这位植物学大家的位置,但是他已年近六旬,再加上时处“文革”期间,他曾是批斗对象,多少还是有些顾忌。不过,吴征镒还是参加了1975年之后的两年青藏科考,并在高原度过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在他身后是他的几代弟子们:武素功、李文华以及一群学生们。吴征镒可以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名称,包括拉丁语学名。多年后回顾这一段经历,李文华还在说,每采得一个标本,总由吴先生当场口述拉丁学名,学生记录。那一阶段的工作最为准确和权威。
初探藏东南

青藏队在林间的宿营地早餐。
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
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四十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文革”中断多年后,科学考察刚刚恢复,孙鸿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
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
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
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
时任行政副队长王震寰,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
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打的比方。哈达寓意吉祥美好,不过用它比作当时的川藏公路,就有些理想化了。
川藏公路即著名的进藏大通道318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318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四十多年前。
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
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
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鸿烈、何希吾、王震寰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
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鸿烈和何希吾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震寰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
“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震寰还这样感慨。
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跃进牌大卡车。四门的北京吉普那时候是县团级领导才有的专车,本来是配给青藏队干部乘坐的,但吉普车越野性强,跑得快,被青藏队用来打前站和“断后”,主要用来联络。孙鸿烈和何希吾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篷,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
小车的车况也不怎么样。王震寰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时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
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震寰就经历过三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那时也是熟读“老三篇”,总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
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
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
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出乎科考队员们的预料。
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公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
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就好像有一个望远镜,再套一个放大镜,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你眼前来啦。”
动物学家冯祚建,在藏东南的密林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
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复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三年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二十多个新属,四百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
……
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科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员百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
及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

青藏队藏北分队登上喀拉米兰山口
成果“井喷”
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孙鸿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四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
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
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峰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昔卡流入印度平原。
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正源。
最早发布雅江源的是斯文·赫定。1907年的那次西藏之行,斯文·赫定由三位当地向导陪同,沿着先前测量的上游诸水系中水势最大的库比藏布骑马上行,直到爬上源头处海拔4864米的山巅。之后,斯文·赫定满怀骄傲地宣布:“全部漫游只花到150马克!谁不情愿这样便宜地买到发现地球上的一条最著名河流发源地的荣誉呢!”
不过,在斯文·赫定西藏之行后的几十年间,雅江源究竟是不是库比藏布一直存在争论,还有双源说——库比藏布、杰马央宗;三源说,在双源说之外加上马攸木藏布。直到69年后,中国的科考工作者来到这里。
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源:北面的马攸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攸木藏布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
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所有的数据都证明,斯文·赫定那次“便宜”的荣誉是个错误,杰马央宗才是雅江正源。
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
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三次穿越过它。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谔、徐近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地、全面地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
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
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外,十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和今后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震寰。王震寰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行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
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震寰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武装”可不只是带着枪装装样子,行前,王震寰领着这些科技工作者到当地部队去实弹打靶,学习使用武器。幸好,这些武器除了动物学家要制作标本时偶尔使用之外,在藏北无人区基本没有用上的时候。
藏北分队倒是被“打标枪”折腾得够呛。“打标枪”是川藏地区的一句俚语,指的是拉肚子。原因无他,水土不服。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三四十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
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一连三天没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
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
历时四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定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四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得区干部大乐:难怪说汉族人吃草。
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青藏高原百科全书

考察雅鲁藏布江源头
1976年10月,当年的青藏高原科考野外工作结束,青藏队收队返程。行至四川雅安,忽见城内大标语“打倒四人帮”,一行人大惊。雅安人奇怪地打量着他们,像看外星人:粉碎四人帮好多天喽,你们咋个不晓得?
“文革”之中,“青藏队是避风港”之说不是没有来由,青藏高原上的科考活动,给科学工作者们创造了一定的自由氛围和学术空间,那是一处虽艰苦却没有纷扰的“世外桃源”。动物学家陈宜瑜院士在回忆中说:“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在野外可以发牢骚,什么都敢说,彼此间很坦诚,大家关系都很亲密。”
几乎与世隔绝的青藏高原科考,也让科考队员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就在他们收队返程之时,“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1976年秋冬之后,青藏队对西藏自治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野外考察告一段落,转入室内研究、总结阶段,为期3年。
1979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成果问世,共30部41册,计2331万字,皇皇巨著,洋洋大观,一部西藏大自然百科全书。这些成果,获得了中科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刘东生和施雅风院士领衔的珠峰考察成果,也在获奖之列。两位院士虽没有直接参加青藏高原科考,却是中国青藏高原研究的领路人。
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巨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的陆续发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了一个“板块构造代表团”,包括8个国家的10位地质学家,到青藏高原考察了一番。虽然时间仅仅两周,却让这些西方学者们大为振奋。中国,这个对西方世界封闭了许多年的东方大国,终于打开了国门。他们回国后,无不对此次中国之行大书特书。于是,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学者向中国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这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现开放姿态的一个契机。中科院筹划了国际性的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文革”后中国举办的首次国际范围学术会议。
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百名科学家和三百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当然,最令与会者惊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出席了此次会议,并接见了与会的中外科学家。
孙鸿烈回忆,那次会议中间召开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招待会,小平同志很高兴,和每一个国际知名专家都握了手,讲一通话。这次会议,恰逢其时地配合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有外国专家提出,希望从西藏采集岩石标本带回国。事情不算大,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相关的政策。有关方面将此事汇报给邓小平。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中国的山那么多,那么大,打一两块石头,大山还在嘛,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嘛!”
一句话,让青藏高原研究的国际合作再无障碍。
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
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功、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索南达杰,就牺牲于此。
20世纪的最后十年,青藏高原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期。第一次青藏高原大规模多学科综合考察结束,青藏高原研究被列入国家攀登计划,这些计划面向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强调了从以定性为主转向定量、定性相结合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过程和机制研究,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综合集成研究,从区域研究转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的研究。
2017年8月,时隔四十余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勉励新一代的青藏队——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希望你们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这样比较两次青藏科考:“第一次是发现,这一次是看变化。”
变化在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首期成果中就清晰可见: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趋好的同时,潜在风险增加;亚洲水塔失衡,冰崩等新灾、巨灾频发;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隆升历史存在明显差异,导致新的生物演化模式……
第二次青藏科考将持续5年到10年,目前还在进行之中。青藏高原这座“地球第三极”,“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需要人类更深的探索、更好的守护。

青藏队队员考察横断山金沙江。
参考资料:《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踏遍神州情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