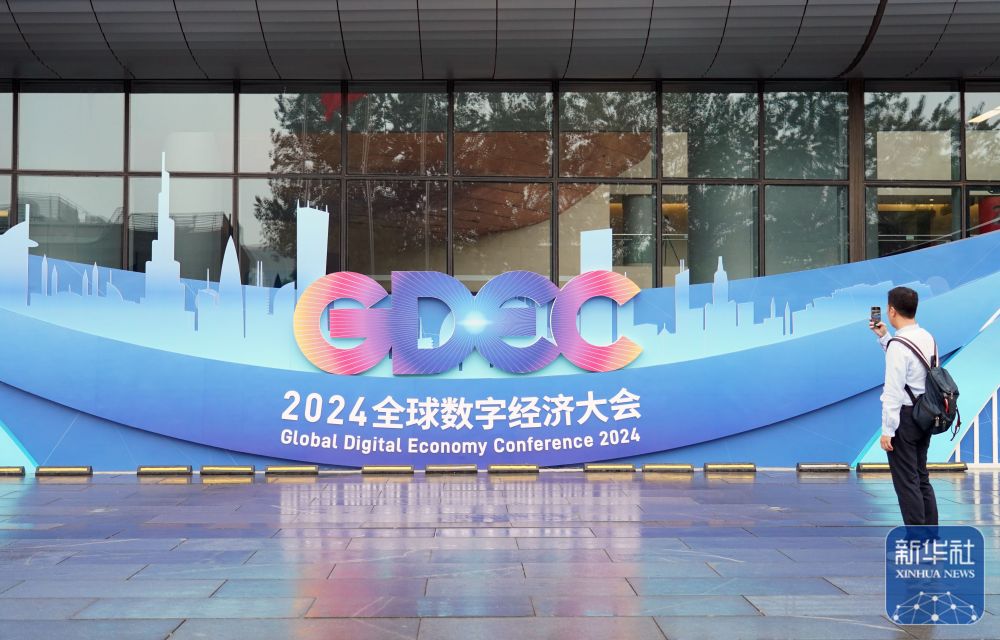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吕雪莉
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在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之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

这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的年保玉则风光(2019年5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记者:您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的先行者,在正式设园之际有怎样的感受?
杨锐:我的感受是喜悦,但更多的是期待。
我从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研究接近30年,是最早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学者之一,从20多岁的毛头小伙干到两鬓斑白。可以说国家公园是我的第二生命,是我愿意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播种的种子、去浇灌的幼苗和去守护的大树,是我珍视的精神家园。因此,听到习总书记宣布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我内心无比喜悦。30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
喜悦之余,更多的是祝福和期待。国家公园是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代中国人的权利,也是每一个、每一代中国人的责任。正式设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我期待中国国家公园坚守“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三大理念,行稳致远,走出中国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

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白水江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大熊猫活动画面(资料图片)。新华社发(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记者:中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有何突出意义?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体现在哪里?
杨锐:国家公园是国家、人民、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国家公园的设立和发展至少具有四个层面的意义: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就人民而言,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国土,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就中华民族而言,它是世代传承的无价遗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华彩乐章;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它将在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缓解气候变化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首先,中国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以管子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代表,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和人、自然和文化从来都不是二元分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次,“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相应地,中国国家公园边界内外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国家公园基本上位于老少边穷地区,必须统筹考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在生态保护第一和最严格的保护前提下,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国家公园治理目标是可行的。去年作为评估组组长,我考察验收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从中看到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治理新理念、新方法与新模式正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成型。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

这是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青海片区拍摄的雪豹(2018年4月14日摄)。新华社发(鲍永清摄)
记者: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建立于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中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有何不同?与之相比,中国国家公园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杨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相比,中国国家公园的时代背景、建设规模和建设难度明显不同。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的建立,其时代背景是工业文明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于1872年在美国建立的时候,“生态学”的概念才刚刚在德语文献中提出,在英文文献中甚至还没有出现。“生态系统”“生态运动”“生物多样性”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对“国家公园”十分重要的概念则先后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生态文明”的概念更是于21世纪初才在中国发展起来。就世界范围来讲,“国家公园”的概念早于“生态”相关概念,国家公园的实践也早于生态运动和生态文明的实践。
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时,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叠加生态文明、工业化叠加信息化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同时生态学也已经成为系统的、可以指导自然和生态保护实践的知识体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系统部署和落实的国家;中国还是世界上信息化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也是各种生态保护和修复实践规模最大、类型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这是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草甸峰丛地貌(2021年9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陈泽国摄
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起步阶段就具有起点高和后发优势明显的特征,可以站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高度,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100多年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教训,运用生态学和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建立科学、适用的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和体制。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还具有“大”和“难”两个特点。第一批整合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已经超过美国全部60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未来中国国家公园预计占国土面积的10%,也远远超出了美国2.3%和世界平均3.42%的水平。第一批整合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平均面积为46000平方公里,是美国国家公园平均面积的大约14倍。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公园总体占地规模庞大、个体国家公园占地范围巨大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显著特征。“难”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另一个特点。虽然中国的土地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但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叠加不同形式、不同年限的土地承包制,造成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地区土地权属的复杂程度世所罕见。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虽然几乎都是国有土地,但是这些土地也几乎全部长期承包给了牧民。造成中国国家公园建设难度在国际上独一无二,没有先例可循。

这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天池景色(2020年9月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蒲晓旭摄
记者:这些年您为了国家公园奔走、呼吁,做了很多事情,一定意义上,也见证了中国国家公园的成长之路。请您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
杨锐: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在承担海南三亚亚龙湾规划设计时,我深刻地感受到必须妥善处理好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与旅游之间的关系,这对中国来讲尤其重要。1997年12月至1999年1月,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期间,收集阅读了大量美国国家公园的研究文献,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历史和保护管理情况,也实地考察了包括黄石国家公园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公园。1998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提议在云南建立“大河流域国家公园(Great Rivers National Park)”,云南省邀请清华大学合作研究,吴良镛教授将其扩展成为“滇西北人居环境(含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研究”,我负责其中的国家公园部分。由于TNC拟议中的国家公园边界内仍然居住着几百万居民,因此我建议用“国家公园和保护地”体系替代这个单一的国家公园,即建立由若干个国家公园和保护地及其生态廊道所组成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并改进完善相应的管理机制。
在十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2003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建立完善中国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次完整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体系的战略方针与行动建议,为10年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国家战略的实施,超前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储备。2006年,我受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的邀请担任专家组组长起草《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的五年规划。纲要中所确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类型,后来成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要组成。2014年以来,我深度全面参与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完成了7项关键性咨政项目,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和实施路径被2017年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系统采纳。作为首席专家,我主持了国家公园领域内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通过对“六项特征”“九对关系”和“十个关键问题”的研究,系统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治理路径。
中国国家公园是“国之大者”,是千秋伟业,呼唤我们心胸开阔、目光长远,超越各种形式的个人利益、地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了人类和万千物种共同的家园同道、同志、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