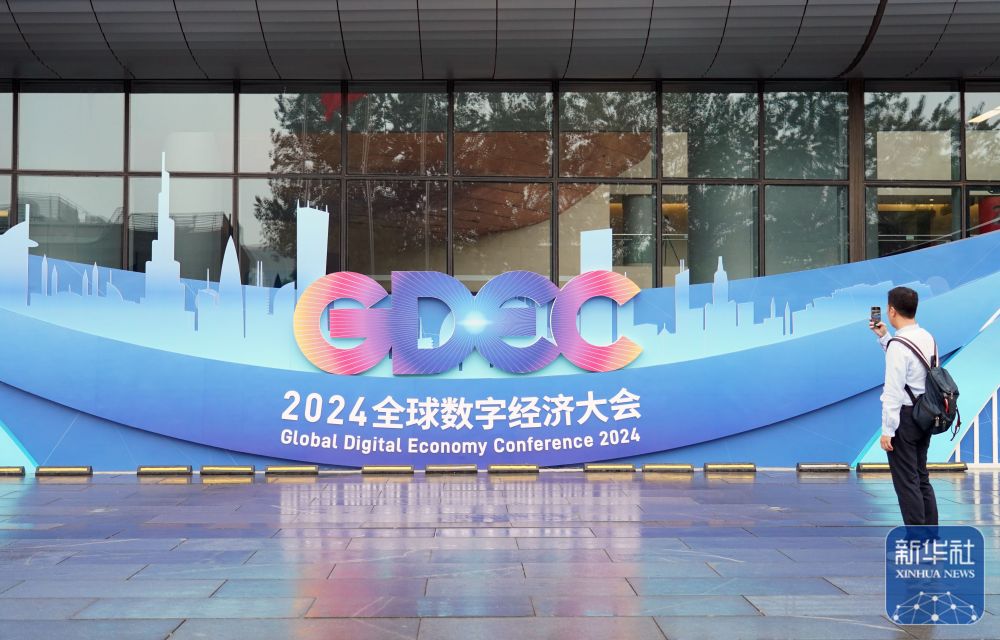——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群众心理疏导;
——把生活保障、医疗救治、心理干预等工作做到位,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愿每一颗受伤的心,都带着爱与希望继续前行。这是心灵“补”手们未变的志愿。
相关阅读
我国近年来出台的心理援助相关政策规定:
2012年6月,国家减灾委员会制定《关于加强自然灾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范灾害社会心理援助的行为,明确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然灾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机制;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中,对开通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作出了具体目标规定;
2016年,22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重申要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和系统化建设;
2018年10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心理援助服务平台”;
2019年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中,有关心理健康的专项行动进一步明确要求,卫生健康、政法、民政等单位建立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等衔接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