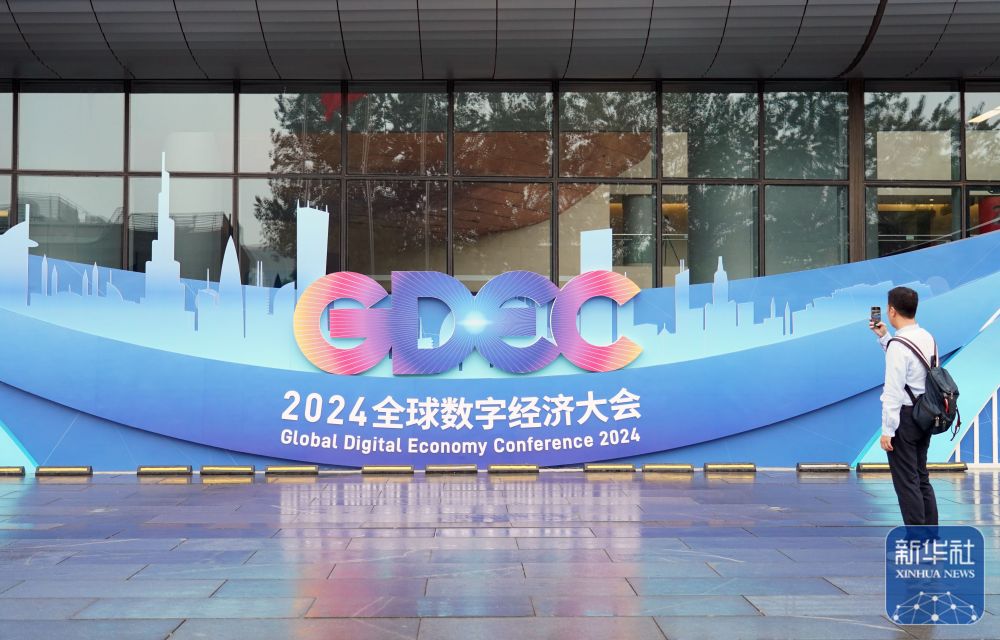“中国天眼”之父走了,留下最美的科学风景 追记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
时至今日,张海燕仍难以接受南仁东离世的事实。她总以为还能再见到那个“似乎无所不知、爱抽烟、嘴硬心软”的老爷子,还能听到南仁东在隔壁办公室喊自己的名字。但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资料图 图为航拍安装完成前夕雾中的“天眼”。 中新社记者 贺俊怡 摄
9月15日,南仁东的生命戛然而止,享年72岁。10天后,由他发起并领导完成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迎来落成启用一周年的纪念日。人们为有“中国天眼”这一大国重器自豪之余,更多了分遗憾——这个工程的最主要缔造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
人们或在报纸,或在互联网上,用“中国天眼”之父、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这样的字眼来缅怀南仁东。而在他身边的人眼中,他更是那个愿意被叫做“老南”的科学家前辈。9月2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专门为老南举行了先进事迹报告会,张海燕是他的学生,也是FAST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说起老南生前的故事,她几度哽咽。
FAST:最美丽的科学风景
南仁东是FAST最早提出者之一。
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与会科学家提出,要在全球电波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
以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南仁东为首的中国天文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在中国境内建造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不到30米。
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副台长赵刚至今记得,从1994年起,当时年近50岁的南仁东开始主持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中国推进工作。这其中就包括他那个大胆的提议,即利用我国贵州省的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
然而,工程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这么大的望远镜建设,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工程,甚至岩土工程等各个领域。赵刚给出了一组数据,2011年开工令下达,在5年半的工程建设过程中,先后有150多家国内企业相继投入FAST建设。工程之复杂可见一斑。
FAST口径达500米,其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8个“鸟巢”体育场。南仁东的想法是,要找一个天然的洼地,不用动用太多土方,且必须是一个远离大城市、射电干扰小的地方。
从选址到2016年FAST正式建成,用了整整22年,其间,南仁东走过数十个窝凼。那时,周边县里的人几乎都认识南仁东——“一开始人们以为发现了矿,后来说发现‘外星人’”。
赵刚说,22年来,南仁东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大窝凼变成一个现代机械美感与自然环境完美契合的工程奇迹,这是他心中一道最美丽的科学风景。
22年,8000多个殚精竭虑的日子。作为“造梦者”的南仁东,从北京到贵州,带领科研工作者、普通工人、农民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实现了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
赵刚援引媒体的一段评价说,他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
“FAST就像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
不少人用“20多年只做了这一件事”,来形容南仁东和FAST的关系。
说起当年勘察台址,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潘高峰谈到了这样一个画面:那时候,南仁东常和年轻人一起,在没有路的大山里攀爬。
在要爬最陡峭的一个山顶前,大家都劝南仁东在山下等着,看完结果向他汇报,他却要和大伙儿一起上去,看看实际情况。潘高峰说:“南老师这么大岁数还要亲自上去踏勘,搞得几个设计院的老总也不好意思,也纷纷跟着爬上去了,其中一个院长还穿着西装、皮鞋。”
那一年是2010年,南仁东65岁。他身穿工服、头戴工帽,走过了贵州近百个窝凼。
也是这一年,FAST遇到了一次近乎灾难性的波折,即索网的疲劳问题。
FAST工程调试组组长、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姜鹏说,当时工作人员购买了十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南仁东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整个研制工作接近两年,经历近百次失败,几乎所有失败案例南仁东都亲自过目。最终,他还是带着团队研制出满足FAST要求的钢索结构,算是让FAST渡过了难关。
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回忆,2014年,馈源支撑塔刚开始安装,南仁东就立志要第一个爬上所有塔的塔顶。最终建成后,他的确一座一座亲自爬了上去。
后来,李辉想明白了:老人是在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庆祝他心中的里程碑!
“FAST就像是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一样,他看着它一步一步从设想到概念,从概念到方案,到蓝图,再到活生生的现实,他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拥抱望远镜!”李辉说。
他的人生充满了执着、义气和随性
有人说,南仁东成就了FAST,而FAST也成就了南仁东。实际上,早在FAST之前,南仁东就已是著名的天文学家。
南仁东1945年出生在辽源市龙山区,1963年,他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成绩、“吉林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是当地10年间唯一考入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文革”之后,南仁东来到北京天文台读天体物理的研究生。后来,南仁东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帮助日本空间甚长基线干涉天文台项目解决卫星-地面VLBI的成图难题。2006年,他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
赵刚说,多年来,FAST的创新技术得到了各方认可,获得了各种奖励,然而,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屈指可数。但他身边的人都颇为默契地认为,南仁东本人并不在意这些荣誉:老南是个人生层次更为丰富的人。
姜鹏后来做了南仁东的助手,接触深入了,经常能听他讲自己的故事:他上山下乡如何度过艰苦而又快乐的10年,他如何回到北京天文台,他又如何在荷兰求学,在日本工作,又是怎样回国的……
“他的人生充满了执着、义气和随性……我太喜欢了,是我多么向往而又可遇不可求的,我甚至嫉妒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姜鹏说。
姜鹏说,老南身上有些品质是自己永远也学不会的,比如怜悯之心:南仁东会以弱势群体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他资助过十余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至今仍有受资助的学生给他写信。他在FAST的施工现场与工人打成一片,他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甚至知道他们的收入。
南仁东的学生、FAST工程接收机与终端系统高工甘恒谦说,南仁东爱烟如命,经常烟不离手。FAST团组里几个较活跃的学生,把这些编成段子。南仁东听到了,不仅不生气,后来他自己还把这些段子拿过来,添油加醋再渲染一番。
当然,该严的时候,南仁东也不手软。
“批评,批评,好像一直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还是批评呢,我甚至有些小情绪。”姜鹏说。
然而,在别人嘴里,姜鹏听到南仁东对他的评价,却一直是不错的。
5月15日,姜鹏给南仁东打电话汇报工作,姜鹏问他:“老爷子,听说你要去美国(看病)?”
姜鹏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南仁东低沉的声音,“是的”。他们沉默了半刻,令姜鹏没想到的是,这时南仁东突然问他:“你有时间回来吗?”
“这边儿事太多了,我可能回不去。”姜鹏没加思索,就这样回复了南仁东。
至今,姜鹏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回答而自责。
在FAST的团队里,不少人都有类似的遗憾。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FAST虽然已建成,但还未产出重大的科学成果。
这也是南仁东的一个遗愿,让FAST这件科学利器早日取得突破性成果。潘高峰希望,那一天,世界各国的同行都将把目光聚焦在这里。潘高峰说到这里,抬头望向前方说,“南老师,这一天,不远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