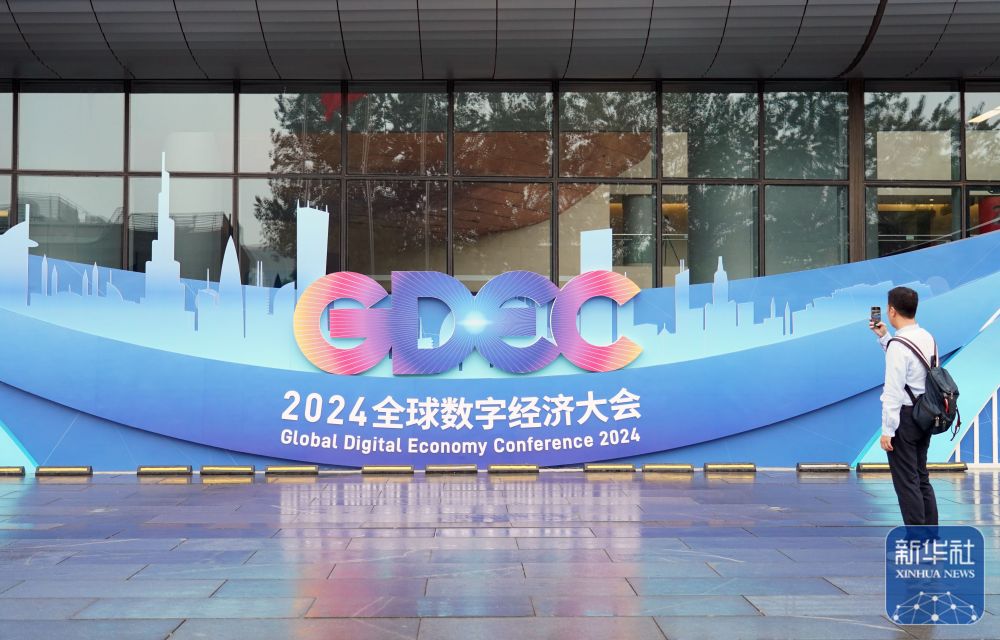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报记者 杨雪 策划 刘莉
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单元,青藏高原被科学界称作“天然实验室”。这里的冰层下封锁着千万年来气候环境变化的蛛丝马迹,湖底则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冰川上白茫茫一片,科考队员的红色衣服格外醒目,一行十几人步履蹒跚,喘着粗气,回到位于海拔5600米的科考营地。11月中旬,第二次青藏科考总队长姚檀栋院士带领的科考小分队,完成了又一次在拉萨河1号廓琼岗日冰川区的考察任务。高原逐渐进入严冬,科考工作将从大量出野外转向以实验室为主,我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也即将进入第5个年头。

科考队员采集湖水样品
有着“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同时,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单元,青藏高原被科学界称作“天然实验室”。这里的冰层下封锁着千万年来气候环境变化的蛛丝马迹,湖底则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为探寻青藏高原蕴藏的地球奥秘,在时隔近50年后,2017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10大任务,260多家单位,7000多名科研人员,1500多个日日夜夜……科考队员们在高山上爬冰卧雪,在河谷中徒步前行,在湖泊中乘风破浪。
他们是“第三极”上的探险家,却无暇欣赏风景。
他们,正在破译埋藏千万年的“青藏密码”。

科考队员调查地质灾害
“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2017年8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第二次青藏科考在拉萨正式启动。启动式上,一封特殊的来信令在场所有的科研人员沸腾——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要求科考队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要“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研究工作。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基础研究八年科技发展规划(1972—1980),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是其中五个核心内容之一;1980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首届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的中外科学家;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最大的贡献”“青藏高原生态十分脆弱,开发和保护、建设和吃饭两难问题始终存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青藏科考,全面完成了260万平方公里的考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参与科考的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等先后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有40余名科考队员先后当选为院士。
青藏高原研究之所以如此受关注,不仅因为它特有的地质地貌和资源,还因为它对周边气候甚至全球环境、资源等带来的巨大影响。
姚檀栋这样比较两次青藏科考:第一次是发现,第二次是看变化。而近几十年,这种变化之快,让研究人员始料未及。
姚檀栋从学生时代第一次出野外,到如今担任科考总队长,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了近半个世纪。他明显感觉到,青藏高原正在变暖、变湿、变绿,降水多了,植被好了,也没那么冷了。“过去60年来,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气候变暖,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地区之一,其升温率超过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
全球变暖,青藏高原气候更宜人,难道不好吗?但姚檀栋看到的却是风险。
果然。
2016年7月,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东汝乡阿汝错湖区冰川群53号冰川发生冰崩。“它几乎是飞下来的,冰体4分钟内向下移动了5.7公里,形成冰崩扇前的速度约每小时90公里。”姚檀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碎冰冲入阿汝错掀起了10米高的巨大“湖啸”,在湖对岸留下了清晰的冲刷痕迹,最远达到离岸250米处。
2个月后,53号冰川南侧的50号冰川也崩了。阿里地区发生这样的冰崩,在有记录以来是闻所未闻的。姚檀栋解释,不同于藏东南冰川的周期性运动,阿里地区的冰川是极稳定的冰川,冰崩与气候变暖直接相关。遥感数据显示,从2011年开始,发生冰崩的两个冰川都出现了上部冰体向下部快速迁移的现象,这说明冰崩的发生有一定积累过程。姚檀栋判断,这种冰崩很可能继续发生,他将这种冰崩看作一种新出现的冰川灾害。
气候变暖导致“亚洲水塔”功能失调,带来一系列生态灾害,冰崩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雅鲁藏布江下游加拉村附近色东普沟发生冰屑堵江;1981年和2016年,西藏聂拉木县樟藏布冰湖发生溃决,对尼泊尔境内造成重大影响……
短期看,是水患加剧,水多了。但据科研人员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流径流的补给将在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减少,长远看,将面临水资源短缺。冰川融水一旦告急,下游干旱区的绿洲将难以为继,气候、环境、植被、资源、人的生产生活统统会发生改变。
“‘亚洲水塔’是亚洲人民的生命塔。”姚檀栋说,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向东西南北不同方向辐散,涵盖青藏高原、帕米尔、兴都库什、伊朗高原、高加索、喀尔巴阡等山脉,面积约2000万平方公里,可以称之为泛“第三极”地区。这一区域关系到全球20多亿人口的生存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的,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
第二次青藏科考聚焦冰川、积雪、冻土、湖泊和河流等关键过程的变化,探索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地球系统科学前沿问题,关系到整个泛“第三极”地区的民生福祉。

科考队员采集岩石样品
“第三极”探险家的日常
第二次青藏科考设立了“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高原生长与演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人类活动与生存环境安全等10大任务,每个任务下还有众多专题。近5年的时间里,7000多名科研人员都在做什么?
11月初,在喜马拉雅北坡希夏邦马峰达索普冰川,随着直升机运下去最后一批冰芯样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柏青完成了今年最重要的野外任务。
冰芯,就是从冰川顶部自上而下打钻得到的圆柱状冰样,它们是冰川研究者的“宝贝疙瘩”。在冰川顶部的积累区,越往下冰层形成的年代越久远。一层一层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可以把地球环境变化信息记录下来。徐柏青是第二次青藏科考中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通过不同冰川的冰芯,揭示这一区域冰川变化和气候变化特征。
冰芯来之不易。徐柏青告诉记者,打冰芯需要在帐篷里作业。但白天阳光一照,帐篷内温度能达到十几度,打上来的冰芯会融化,所以只能夜里打。而冰川上光照尤其强,帐篷不能完全遮住光,晚上工作,白天补觉又困难,他们平均一天只能迷迷糊糊睡两三个小时。
青藏高原有数以万计的冰川,还有数以千计的就像“高原明珠”的湖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朱立平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湖泊与水文气象考察队负责人,在给这些大大小小的“高原明珠”“做体检”。
“用遥感技术可以知道湖面有多大,但湖水多深不知道,湖水是淡还是咸也不知道。所以,就要测量这些湖泊,进而掌握储水量、水质等数据;再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就能够预测这些湖泊未来的变化。”朱立平说,他也需要打湖泊钻——乘坐橡皮艇来到湖中央,爬上用浮筒或者浮箱搭建起来的约十几平方米大、可载重3至5吨的作业平台,把活塞采样器放下水,穿进湖底的泥里,得到一个岩柱。从这个岩芯中的湖底沉积物,可以读取气候变化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邓涛行走在古遗址中寻找化石证据,来还原远古时期动物和人类的生活场景。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杨永平穿梭在森林和草原之间观察花花草草,给高原珍稀植物建立档案……
科考启动近5年来,来自260多家单位的科研人员在野外和实验室来回切换,中秋节、国庆节甚至春节都经常是在野外的帐篷里过的。
科考队估算了青藏高原储水量——包括冰川水储量、湖泊水储量、主要河流径流量,总和超过9万亿立方米。并预估21世纪末,如果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青藏高原将升温2.1摄氏度,冰川将消融三分之一。
科考队发现,横断山区—祁连山森林分布区过去100年树线位置平均上升了29米,最大上升幅度80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朴世龙说,高山树线上升增加了森林生物量,但压缩了高寒灌丛、草甸的生存空间,增加了高海拔特有物种消失的风险。同时受青藏高原增温影响的还有藏族人民的主要食物青稞,2000年以来,温度每升高1℃,每公顷青稞产量降低0.2吨。
科考队在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土壤沉积物中,获得一系列有关生活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的人类种群——丹尼索瓦人长期在青藏高原活动的证据,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最早活动历史推至距今19万年。
……
近5年来,科考队还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利用系留浮空艇、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直升机等,初步建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化治理地球系统科考平台。“这是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科考平台,大气圈、冰冻圈、水圈、生态圈、岩石圈、人类圈所有这些圈层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在同一时间完整记录下来。”姚檀栋说。

科考队员背着钻取的冰芯样品下山
传承“青藏科学精神”
守护这方净土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应该说,太难了。
直升机运输,是近两年才在希夏邦马达索普冰川和阿尼玛卿唯格勒当雄冰川用上的。此前打冰芯,全靠人力运输。徐柏青说,他们通常要往返于海拔5000多米的前进营地和海拔7000多米的冰芯钻探营地之间,送上去物资,带下来冰芯。
静谧的高原湖泊也不是想象的那般风平浪静。朱立平说,打湖泊钻,如果遇上大浪一起,人在作业平台上就站不住了,遇上风浪最大的一次,回程时船是呈45度角“切”着浪走的,“学生在船头拿盆不停往外舀水,我在船尾开船,最怕发动机熄火,给油要恰到好处,油加太多会‘憋死’,油不够就会熄火”。回到岸边营地时,他们的冲锋衣、抓绒衣、秋裤等里里外外的衣服全部都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针对2018年雅鲁藏布江下游加拉村附近色东普沟发生的冰崩堵江事件,2019年10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威和同事徒步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原始森林,在堵江事发地安装了10米高的监测塔,前后在野外住了十多天。“西藏东南部地区很潮湿,虫子很多。夜里睡觉时,要在帐篷外再罩一层塑料布,但还是总被蜱虫咬。”杨威说,蜱虫跟蚂蟥一样,往肉里钻,得拿烟头烫一下才能把整只蜱虫拔出来,否则头留在肉里不好办。
……
尽管新时代的青藏科考有一系列新科技装备加持,但高原反应、极端的野外环境、种种危险等客观困难是必须靠人来克服的,而进入冰川、湖泊、森林开展考察工作,人力始终是不可替代的。最令人恼火的是,仪器也有“高原反应”。受高原特殊的气压、湿度、温差等气候环境影响,很多仪器上了高原就会失灵,有时候,科考队员辛辛苦苦采集的数据,说没就没了。
记者采访过的每一位在青藏高原做研究的科研人员,身上都有一种相通的气质:乐观、豁达、热爱野外、特别能吃苦。他们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协力攻坚,勇攀高峰,这是我国老一辈行走在青藏高原上的科学家开创的、并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青藏科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伊始,青藏高原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研究,只有极少数的外国探险家和传教士收集过一些零星资料。从那时起,青藏高原研究就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科研任务。科学考察工作也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展开,对局部地区自然条件、地质、农牧等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科考。
1973年,第一次青藏科考大幕拉开,由著名地理学家、土地资源学家孙鸿烈主持。基础条件差、物资匮乏的岁月,400多人毅然投身科考事业,啃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最好的投宿地是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住双层大通铺;无数次前方无路,无数次下河推车……4年时间,从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无人区,从横断山脉到阿里高原,科考队员几乎用脚步丈量了青藏高原全境。
这支特别能吃苦的青藏科考国家队,开拓了青藏高原的科学大发现,也为尔后的青藏高原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这种基础不仅是科研工作本身,还包括工作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考队员进行高寒草甸调查
“第三极”研究看中国
青藏高原这块土地的神秘曾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这样形容:“到1907年1月为止,我们对行星面上的这部分(青藏高原)与对月球背面同样一无所知。”100多年后的今天,在科学家们的探寻和仪器设备的测量下,青藏高原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无力组织大规模科考,到如今组织数千人、预计长达10年的第二次大规模青藏科考。今天,中国的青藏高原研究走上了世界舞台,并敞开怀抱,与全球各国科研机构携手。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受益于各项中外联培计划的科研人员,为青藏高原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面向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开始从以定性为主转向定量、定性相结合,从静态转向动态、过程和机制,从单一学科转向综合集成,从区域转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
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对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其在全球生态环境中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2009年,姚檀栋联合国内外“第三极”研究科学家共同发起“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致力于推动“第三极”地球系统多圈层研究,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
美国伯德极地研究中心朗尼·汤普森教授是“第三极环境”的联合主席之一。这位“第三极”的“好朋友”,疫情之前几乎每年都要上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尽管已经70多岁,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另外两位联合主席是德国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古生物学家福克·莫斯布鲁格教授和姚檀栋。
“第三极环境”每年开一次例会,约定往后在尼泊尔、印度、美国、德国开,各国轮流做东。但2011的年度例会竟然是在冰岛开的。原来,冰岛总统听说了这一计划,希望与北极研究结合起来,特发出邀请。
这种跨国家、跨地域、跨学科联合研究的方式,把欧美研究者擅长的模型、方法引入“第三极”地区,同时共享更多野外一手数据,推动研究领域整体发展。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论文数量和引用率稳居世界第一。世界极地科学圈中,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极”研究作为一支崛起的力量备受关注。
全球都在关心气候变化,科学共同体期待来自“第三极”的声音。接下来,第二次青藏科考将继续聚焦“变化”,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何整合各类观测与模型,预测气候变暖下亚洲水塔未来的命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给周边地区带来什么影响,如何应对?青藏高原是怎样响应全球变化的?高原生态演化与人类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青藏科考数据共享平台、青藏科考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平台等也都在建设中。
科研人员们还将继续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探索,努力解开藏在这里千万年的秘密。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