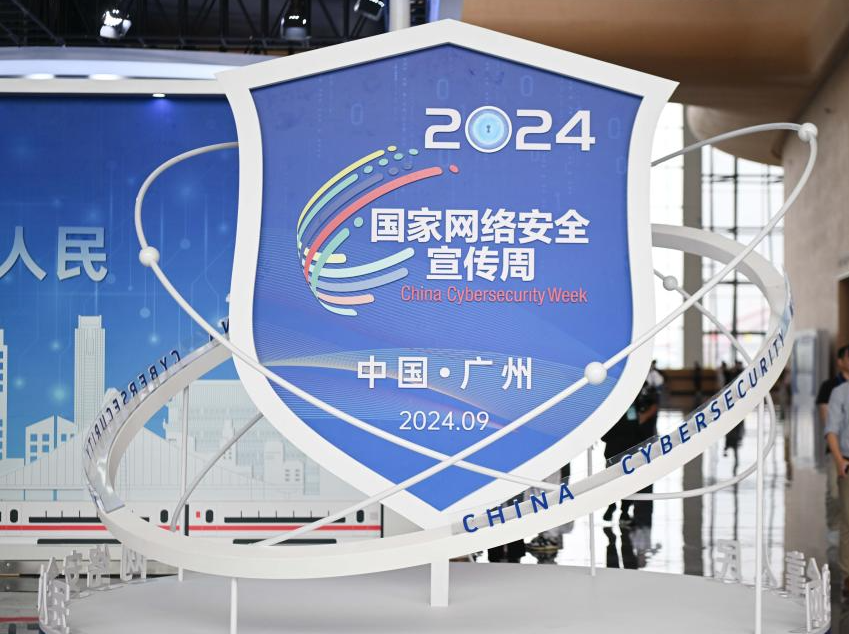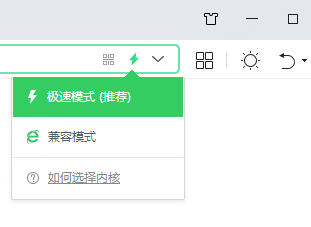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报记者 王迎霞 实习生 李雨函 策划 赵英淑 林莉君 滕继濮
水洞沟遗址横空出世,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曲,从而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遗址群。古人类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物、遗迹。

水洞沟遗址。视觉中国供图
盛夏的西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射向大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郭家龙就已经爬上了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附近的最高处。
“太阳没升起前,光线是最柔和的。”为了获得珍贵的影像资料,郭家龙前一晚专门住在了考古工地。
水洞沟遗址有考古工作者造访的历史百年可溯。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去往内蒙古鄂尔多斯调查研究古生物的途中,偶然发现了这里蕴藏的大量旧石器、动物骨骼化石等。他们便留下来,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古发掘。
这次偶遇让水洞沟遗址横空出世,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曲,从而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遗址群。古人类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物、遗迹。
距今4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水洞沟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百年来,其神秘面纱正被徐徐揭开。

第1地点出土的石叶。

第2地点出土的鸵鸟蛋壳装饰品。
读一本“地书”
驱车出银川,一路向东。
黄河贯穿平原,奔流不息;沙漠覆盖大地,绵延不绝。到了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遗址就在眼前。
人类起源于何地,又是如何在世界留存脚印的?这是考古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
“考古工作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是发掘研究深厚地层里的遗物和遗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高星说,“我们把这称之为‘地书’。”
层层叠叠的地层是一张张“书页”,而地层里的遗物和遗迹,则是书写远古历史的“文字”。
“通过解读这些‘文字’,我们对水洞沟人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有了一定认识,也知道了他们当时面临怎样的资源环境条件。”高星说。
北京人、蓝田人、山顶洞人,很多人通过中学历史课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然而,关于水洞沟人,见不到只言片语。
“在大学的专业课上却不是这样。”宁夏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李昱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本科一路读到了博士。站在专业角度,他强调,水洞沟人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群体。
走进遗址公园,一块硕大的石头上,“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字样赫然在目。
水洞沟遗址的芳容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就打消了对于中国是否有旧石器文明的质疑。
1923年的那次发掘,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总量达300公斤以上,鬣狗、羚羊、牛、犀牛和马等均见其踪。
在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出土了大量使用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器。勒瓦娄哇技术是古人类制作石器的一种技术,最早发现于法国,盛行于整个欧洲及西亚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20万年到3万年左右。
该文化性质的遗址在我国非常罕见,只有3处,另两处分别在内蒙古和新疆,都是2012年以后才被发现。而这一“舶来品”早在八九十年前就现身水洞沟遗址,从侧面印证了东西方人类之间的交流与迁徙。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水洞沟遗址的考古工作自此按下了“暂停键”,直至新中国成立。
1960年,我国和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水洞沟。
1963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裴文中,带队前来进行了又一次发掘。正是这次发掘,考古队员首次发现了第1地点包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
“这里不仅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还有新石器时代文化,说明人类文明在这里是持续发展的。”李昱龙说。
1980年,为了进一步探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文化内涵,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考察队进行了联合发掘。在38天的时间里,共发现了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标本。
2003年,水洞沟遗址迎来了陪伴它最久的朋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星带领着他的团队进驻宁夏,两个研究所开启了长达20年的合作。
随后5年,他们发掘了水洞沟遗址第2、3、4、5、7、8、9、12地点。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的新方法、新理念,首次得到大规模运用。
李昱龙称,这是在“摸清家底”。
2018年至2022年,考古工作者又对第1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系统化发掘,目前相关研究工作仍在继续。
这一次,考古人员彻底明确了第1地点地层的堆积序列,从中采集了大量测年样本,出土了包括火塘、石制品、动物化石等共计1万余件。

第12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骼。
那些前尘往事
犬牙交错的土石,光滑平整的剖面,清理完毕的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掩映在茂密芦苇之间。
只有一层一层不规则的“花纹”,昭示着古人类生活的印记。
“别看这里现在荒芜,在距今4万至3.8万年左右,水草可丰沛呢。”郭家龙告诉记者,据研究推断,如今的边沟河在当时是一片古湖,水洞沟人在这里制作石器、狩猎动物、采集植物。
水洞沟人在此生存的时候,正值全球环境变化较冷时期。水洞沟又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所以有很多沙地、丘陵、草原。同时,水洞沟还处在黄河边上,又有很多湖泊。其地势是盆地,还有很多湿地和水塘。
环境如此多样,造就了水洞沟局部动植物资源富集的生态条件。
“我们从遗址里发掘出很多大型哺乳动物,骨骼都比较破碎,有工具切割的痕迹,这是人类狩猎然后敲骨吸髓,充分食用和利用了这些动物食物资源的结果。还有一些动物骨骼被人类作为原料加工成工具和武器。”高星说。
在利用植物资源方面也是一样。
考古人员在地层里发现了孢粉和植物果实,通过对现生植物观察发现,附近应该有二三十种可食性的植物食材,水洞沟人工具上的残留物也表明了这点。
丰富的风化岩石是远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白云岩、石英岩、石英砂岩。“这些材料对他们的生存非常重要,这也是4万年以来人类不断在水洞沟生存演化的原因。”高星指出。
然而在距今2万年左右末次冰期的高峰期,水洞沟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因为气候特别恶劣,他们迁移到了更温暖的地区,气候转暖后又回到了这里。
与第1地点隔路相望的是第2地点,走路只需短短几分钟。可是在几万年前,水洞沟人花了万年才“走完”这段距离。
第2地点的规模不像第1地点那么大,时间为距今3.3万到2.7万年左右。从中出土的遗物的意义不容小视。
水洞沟人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行为,比如说集中聚落式居住。
“这跟后期的定居还不一样,我们的证据就是在第2地点还有其他地点发现有密集分布的火塘。这表明在一定时期,人类在这里生存且具有一定规模。”高星说,“水洞沟人的技术也在变化。”
“这一时期,他们所运用的技术是小石片技术,这是中国本土连续进化的一种石器技术,与100多万年前北京猿人所使用的技术一脉相承。”李昱龙解释道,“本土延续进化的特点也标志着中国现代人的起源。”
高星特别强调,用火在这个地方非常出彩。
水洞沟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把一些石头放到火里烧烤以后,石头质地结构会发生改变,然后制作出规整锋利的石器。
“用火来改造原料是一项重要发明,后期陶器制作、金属器物制作都是这种技术的延续。”高星补充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明技术的开端。”
技术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审美能力的提升。
第2地点的古人类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现代人的行为特征——利用鸵鸟蛋壳加工装饰品、制作骨器、石器原料热处理等等。
两个地点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以吴新智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现代人起源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论断。“虽然近在咫尺,但目前并没有发现第1地点和第2地点之间的联系,这也是未来探究的一个方向。”李昱龙说。
第12地点的发掘,则将历史的扉页翻至了距今1.2万至1万年。
这一时期的水洞沟人,狩猎采集行为越来越复杂,食谱愈加丰富。除了大型哺乳类动物,小型哺乳动物如兔子及水生动物、贝壳,也成了他们的采集对象。
水洞沟人并非纯粹的茹毛饮血者。他们知道将石头放在火上炙烤,再把滚烫的石头放入水中会让水迅速升温沸腾,沸腾的水便可以用来烹煮食物。
这是中国唯一能够证明“石煮法”被古人类应用的遗址。而古人类获取食物的手段更加先进、处理食物的能力更加复杂,业内称之为“广谱革命”,即农业产生的必要条件。

第12地点出土的细石叶。
考古不是“刨土豆”
年代的久远,科技的匮乏,都一度是掣肘水洞沟遗址发掘的重要因素。
“以前受科技手段所限,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发掘过程中主要以文物石器、动物骨骼为主,至于微小的标本采集以及遗物的空间分布,根本无从谈起。”带记者参观的路上,郭家龙忍不住慨叹。
1980年,宁夏考古工作者有了新的“伙伴”——各种科技手段隆重登场。随着铀烯测验方法和碳十四测量方法被首次运用,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获得了水洞沟遗址相对科学的年代数据。
如今的水洞沟饱经风雨侵蚀,曾经的它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要想探究,必须依靠科学方法。
植物孢粉分为孢子和花粉,虽然用肉眼难以看到,但可以保存很久。孢子和花粉的外壳非常坚硬,既耐盐碱又耐腐蚀,在几万年的地层中形成了孢粉化石。不同植物的孢粉有着不同形态。通过采集植物孢粉,可以将这片土地上曾经生长过的植物逐一铺展开来。
在第2地点的考古研究中,考古工作者就大量使用了植物孢粉研究技术。他们将土层从上到下划分为47个连续的孢粉层,逐一观察发现,第2地点在旧石器时代地貌的总体特征是荒漠草原。
当然,孢粉由于轻、小等特点,即使在这里发现了某种植物的孢粉,并不能百分百确定它就是“土著”,也有可能是“移民”。
步入新世纪,水洞沟遗址开启了连续性发掘期,新理念、新方法的运用成为主旋律。
“没有无人机之前,想拍一张遗址的整体空间分布图,要爬到很高的梯子上。想拍一张包含遗址周围山川河流关系的大范围照片,更是难上加难。”郭家龙说,“自从有了无人机,这些都不是事儿。”
在新一轮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不再只关注单个文物,而是侧重厘清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从而描摹出水洞沟人生活的空间蓝图。
“我们发掘到的文物是不能动的,等清理出一个平面,要进行拍照、测量、绘图,才可以将它们彻底发掘出土。”李昱龙说。
空间分析理念像是一根引线,将水洞沟遗址的各个文物串联起来,让散落满地的“珍珠”重新各归其位,成为美丽的“珠串”。
于现代考古而言,最重要的是真实科学地记录。
“不能老想着要挖出什么。这不是刨土豆,你挖一个就装一个。”李昱龙笑着说。
全站仪被首次应用在水洞沟遗址考古当中。它像是一台超能的摄像机,将水洞沟人生活的场景复原。
遗迹发掘出来,利用全站仪给遗址建立一个三维坐标系,明确每件遗物的位置及遗物之间的相对位置。遗物的长度、倾向角、埋藏深度一一被测量,包括是否受过流水的影响、经历过地震,都能精准展现。
通过全站仪,考古团队建立了关于水洞沟第2地点遗物立体分布的数据库。这对于管窥水洞沟人的生活无疑是重要之举。
全站仪的应用对考古发掘工作来说已然是一次跃升,数字化发掘更让它搭上了科技的快车。精妙之处在于,以前只是单纯地用全站仪进行测量,现在则将它与数据库、3D建模系统连接在一起。
考古发掘现场测量到的点,立刻通过电脑转移到数据库,再辅以拍照、摄像等,一个立体的遗址模型便做好了。并且每一次发掘所建立的三维模型可以通过电脑整合在一起,待发掘完毕时,整体的三维模型及遗物遗迹数据库即可呈现。
在水洞沟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不断探索、创新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发掘流程。目前,这一工作流程也正从水洞沟走向全国。

第12地点出土的热处理石制品。
遗憾的魅力
“有些遗址一辈子都挖不完。水洞沟发掘到今天,我们还有遗憾。”留驻考古工地的郭家龙,戴着一顶遮阳帽,面庞黝黑暗沉。
他与水洞沟已经朝夕相伴了10个年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已经深深刻入了他的脑海。
“印象最深的是清理火塘,因为火塘周围遗物分布特别密集。”那也是郭家龙第一次在水洞沟清理出文物,欣喜自不待言。
另外一次令他久久难以忘怀的,就是发掘出马鹿牙齿。带有钻孔的马鹿牙齿装饰品彰显了古人类的审美能力,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郭家龙当时就意识到,“这可不得了”。
因为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水洞沟遗址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作用。
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正如郭家龙所说,遗憾也是一种魅力,水洞沟仍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世人探索。
旧石器时代人类流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迁居式,另一种是后勤式。迁居式就是不断搬迁,在某一地点短期居住,与游牧民族的营地相似;后勤式则是古人类建立较大的“后勤大本营”,虽然去往不同地方狩猎采集,会建立小的营地,但终会回来。
“在第1地点发现了古人类生活的聚落,但并不足以说明他们在此定居。水洞沟人是何种流动方式,仍是考古学界的重要课题。”李昱龙说。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尚未发现古人类化石。
早些时候,虽然在第1地点修路的过程中发现过一块人的头骨片,但不是正式发掘出来的。由于脱层,它的时代不是很清楚,而且骨骼较小,不能对其形态进行研究,对遗传信息很好地提取分析。
“未来,假如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地层里找到人类化石,那么水洞沟人到底是本土人,还是有一定混血或者是有外来人群的迁徙共同演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应该会有眉目。”高星的语气柔和而坚定,“我们肯定会继续发掘研究。”
水洞沟遗址不仅是考古研究的宝地,更是一个野外的“课堂”,包括郭家龙、李昱龙在内的年轻人都从这个“课堂”走出。
自2003年开始,水洞沟遗址考古队就注重对旧石器考古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当年进驻的队伍,除钟侃和王惠民两位年龄较长的专家外,其他均为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
这一工作模式也使得水洞沟遗址继周口店遗址后,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个人才培养基地。从水洞沟走出的新一代学子,许多已经成长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中坚力量。
在第2地点,郭家龙正在指导工作队对一些沟隘的边边角角进行抢救性发掘。他透露,目前水洞沟考古发掘的面积非常有限,地点也非常有限。
这恰好与高星所言相吻合。“一方面是力量有限,这种精耕细作的发掘,进展非常缓慢,假如发掘面积很大,根本做不过来;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更多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学者,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和研究能力。”
“留下大量空间,也是为未来的发掘研究奠定基础。”高星说。
几万年来,风吹过又走,雨下过又停。读懂水洞沟,中国考古人在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