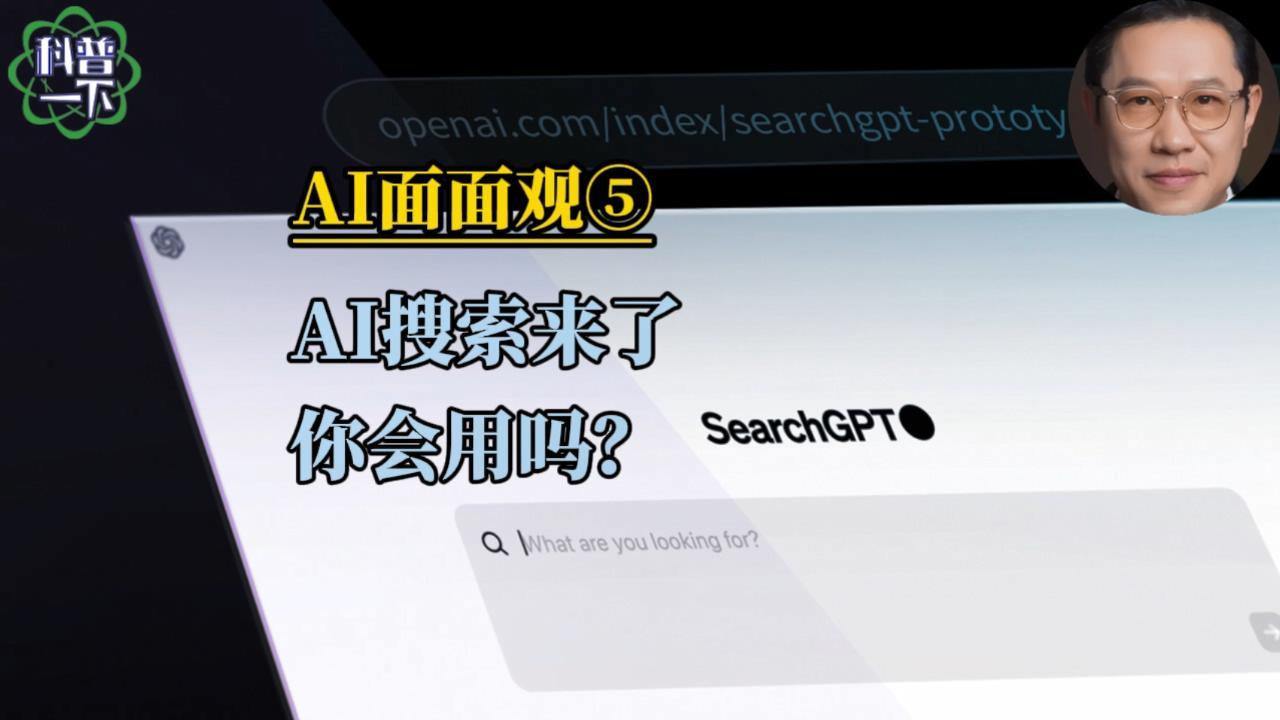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便是其中之一。”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曾这样写道。
“罗哲文”是一个公众可能并不熟悉的名字。然而,长城、北京团城、赵州桥、炳灵寺、布达拉宫……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文物的保护与修缮工作中,都曾有他奔走的身影。
近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故宫博物院主办,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管理委员会承办、中国文物学会等相关单位支持的“业守精勤 匠心永驻——罗哲文百年诞辰纪念展”开幕式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展览上,罗哲文生前出版的书籍、珍贵手稿,使用过的相机、卷尺、测绘物品和63组为致敬罗哲文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共同展现了他为文物保护事业奉献的一生。
敢于坚持原则的“文物卫士”
1924年,罗哲文生于四川宜宾。1940年,他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是中国营造学社最后一名社员。1950年,罗哲文调入政务院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工作,此后,他一直奔波于祖国辽阔大地星罗棋布的古建遗存间,组织保护,审定维修,阐述学说……
在7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罗哲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保护文物古建免遭人为破坏,成为中国乃至国际文化遗产界备受尊崇的斗士。
罗哲文的儿子罗杨回忆,父亲生前,家里就像“文物保护120”,只要接到哪里的古建要被拆了,哪里的文物要被毁了,哪里发现了古建遗迹的电话,父亲二话不说,背上三台形影不离的相机就出发。
罗哲文一生拍下了数万张珍贵的文物和古建筑照片。
团城是北京城内的一块瑰宝。历史悠久,也是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都城的重要见证。1953年,为拓宽道路,有人提议拆毁团城。文物保护界就此打响了一场“团城保卫战”。
1954年初的一天,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给罗哲文布置了紧急任务,让他赶紧写一篇关于团城的报告。罗哲文连夜埋头工作,连轴奋战了两个多月,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等详尽的关于团城的报告交到郑振铎手中。此文随后在《文物参考资料》杂志发表,成为保护团城的有力依据。
此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到团城考察,决定让马路稍微转点弯,避让团城。多方努力下,团城得以保留。
北京古观象台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且具有完整仪器和观测记录的古天文台,在世界范围内都独一无二。因修建地铁,建设部门曾提出拆除或者搬迁方案。罗哲文与同事认为,古观象台位置的改变将损害其历史观测数据的价值,于是自发进行实地考察、测绘和摄影。他们以普通群众名义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保护报告,最终在总理亲自过问下,古观象台遗址不仅保住了,还获得了专项资金进行基础加固。
为更好地保护文物古迹,1981年,罗哲文与同仁首次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概念;1985年,他推动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参与1986年首次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此后,罗哲文又推动京杭大运河、平遥古城等多处遗产成功申遗……
全国政协原秘书长、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卞晋文感叹,在大兴土木、国门初开的阶段,在大规模开发性工作与文物保护发生冲突时,罗哲文和他那一代文物工作者,不畏困难,不言放弃,守护了中华文脉。
古建筑保护与维修的领军人物
罗哲文是全国古代建筑保护与维修事业的领军人物。
“有多少将帅元戎、戍卒吏丞、百工黔首,费尽移山心力,修筑此伟大工程。坚强毅力、聪明智慧、血汗辛勤,为中华留下丰碑国宝。”这是罗哲文曾为长城写下的文字。
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建议维修长城,后来,罗哲文接到了这一任务。他带队重点勘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长城,经过3个月的实地勘察并广泛查阅资料,取得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罗哲文绘制了一份八达岭长城的维修规划,并请梁思成审定。规划获批后,罗哲文协调各方,仅用1年多时间就完成修复,使八达岭长城重现雄姿。
随后罗哲文又相继主持和参与了居庸关、山海关、金山岭、慕田峪、司马台、九门口、玉门关等地长城的修缮工作。全国所有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长城修复工程中,都或多或少倾注了罗哲文的心血。他也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罗哲文不仅参与了长城的维修工作,还参与了故宫的保护规划、百年大修、建福宫花园复建、故宫文物库房建设等重要工作;参与、主持、指导了蓟县独乐寺、布达拉宫、塔尔寺、罗布林卡、萨迦寺等古迹的修缮工作;并长期承担古建筑保护维修培训的组织和教学工作,常在清华大学等高校授课,培养了一大批古建筑保护维修的专业人才。
1989年,布达拉宫迎来300年来首次大修。整个修缮工程历时5年8个月,修缮项目达到110余项。1994年,布达拉宫重放光彩,并于当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罗哲文亲历了这次工程。他不顾高龄和高原缺氧带来的不适,从1985年开始,几乎年年都要进藏。从现场勘察、方案审定、施工检查到工程验收,一丝不苟,恪尽职守。
“罗工一辈子都在为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忙碌,经常刚回家一两天,收拾收拾又去往别处。”罗哲文的老同事、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黄克忠回忆,“有一次罗工跟我讲,1个月不到,就已经出差了7次。”
2003年,尽管已经八十岁高龄,罗哲文仍跟年轻人一起进入了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的新疆楼兰古城遗址。回来后他高兴地说:“小罗八十进楼兰。”
卞晋文说,从罗老身上,他看到了热爱。“这份热爱不仅仅是对砖石木瓦的欣赏,更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敬仰。他这份热爱也直接影响了与他共事、与他交往的同志。”
罗杨坦言,文物工作者不像运动员,能为国争光,能留下一个个精彩瞬间;也不像影视明星,能得到那么多人追捧。他们大多“择一事,终一生”,默默坚守,无私奉献。
2012年5月14日,罗哲文在京逝世。同年,他被安葬于八达岭陵园,与他挚爱的长城长久相依。
每一个文化遗产的背后,都有一段段闪光的、充满智慧的感人故事。“我希望大家看完展览后,会更加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有更多人愿意加入守护文化遗产的行列,把父亲所走的路,继续走下去。”罗杨说。